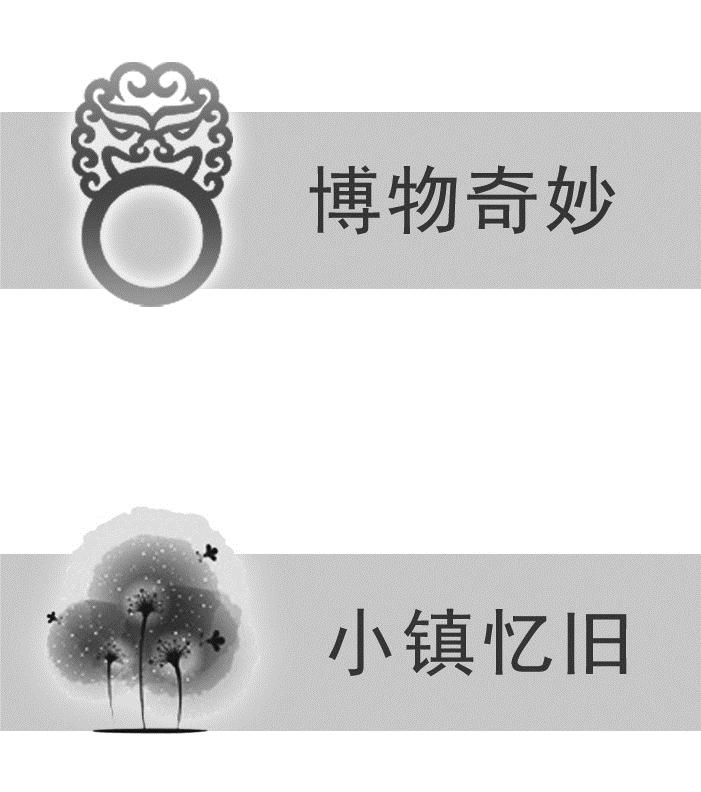我没想到泥土会像棉被那样柔软,充满温情,让人迷恋。接着,我又爬上树。我爬上树,只是为了纵身跳下,扑向泥土的怀抱。
□刘剑波
艾哈迈德·拉西姆说,每当我回首旧日,重温过往,我仿佛总会看见一群人漫步于黑暗中。而我会说,每当我回忆小镇,眺望过往的人和物,我仿佛总能听到马路上传来的各种声响。从前,小镇鲜有汽车和卡车,马路负载的是自行车、独轮车和手扶拖拉机,以及各种各样的脚步。那时的马路还没有铺上柏油,只是在土质上铺了一层沙砾,更早些的马路则十分原始,名副其实的土路,路面上壅积了半尺厚的塘灰,随风扬起。天气晴好的日子,在上面行走,简直就是在沙漠中跋涉。每当公共汽车从小镇南面的招呼站方向驶来,人们会看到一条逶迤的灰尘巨龙被拖曳着,由远而近,它想飞起来却总是功败垂成,于是一直保持欲飞未飞的姿态。在马路两侧农田忙活的农人,会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这条仿佛能够触手可及的巨龙从眼前一闪而过。观看这样有趣的景象,是我们小时候的娱乐活动之一。我们拍着手,站在马路边上大呼小叫着,泥龙,泥龙,泥龙来了!
等到公共汽车近了,我们会听到马达的轰鸣。我们会觉得那其实是泥龙不耐烦的吼叫。它太有理由不耐烦了——它从掘港一直被拖着来到小镇,这事搁在谁身上都会不耐烦。等到公共汽车在车站那儿停稳——吴杭州早已手拿开车门的大钥匙在路边等候——泥龙倏然消失,仿佛钻到地下遁走了。但其实它无处不在:挨近马路房子屋顶上的瓦楞草在风中摇曳的姿势变得沉重了;我家院子围墙上自然长出的绿色植物一下变得灰蒙蒙的了,而窗棂和门楣上被洒上一层虚浮的尘土。爱干净的陆善堂总是在泥龙抵达前的那一刻躲进屋内,关紧了大门。等到泥龙在车站路边喘息甫定,他才拉开大门,这时他会发现,他紧靠马路边的露天修车铺有了变化,比如,撂在地上原本擦拭一新的修车工具不再锃亮,不仅如此,它还被一层泥土遮盖起来,仿佛有一只手正在将它们掩埋。今天小镇上的孩子再也不会看到泥龙了,不过,也许它会出现在这些孩子的梦境里,因为历史是从来不会消亡的,它一直隐藏在时间里。当那条象征着小镇历史的泥龙出现在孩子们的梦中时,他们也许会惊惧不安,他们会喁喁细语,那是什么啊?然后,从那个年代走来的长辈会抱起他们,说,从前有一条泥龙从掘港而来,但它并没有翱翔在天,而是蜿蜒于大地……
在这条沙漠般的马路上行走,无法不深一脚浅一脚。鞋子里会灌满沙土,裤脚上会沾满泥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下午,我和姐姐带着幼小的弟弟,从马路上往南走。正蹲在门口修自行车的陆善堂自言自语,刘家小鬼又要去接娘了。他的启海话刚劲有力,掷地有声,很像京剧舞台上的武生念白。在我对小镇的回忆里,陆善堂总是在修车。他有时蹲着,有时坐在小凳上,有时则俯身于正在修的自行车上。我一直很怀念陆善堂,他长得很像鲁智深,魁梧,络腮胡,胸脯有浓密的体毛,为人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我家两个邻居都是修自行车的,还有一个是陈希芳。陈希芳高身量,白皮肤,一头黑发,称得上是美男子,然而,这一切都被他的面相破坏了:他的三角眼和鹰钩鼻给人以不怀好意和奸诈的感觉。如果在陆善堂和陈希芳当中选一个当镇长,我会毫不犹豫把票投给陆善堂。
陆善堂说得没错,我们姐弟三个是去迎候在县城人民医院上班的母亲的。我们走过王奶奶家西山头,又走过陆炳龙家西山头,一直往南。我们走到去“东海部队”的路口,还是没有停下来。我们往南走得很远,都快要到招呼站了。要不是弟弟走不动了,我们还会一直走下去,说不定会一直走到掘港。我们都没去过掘港。掘港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神秘而激动人心的地名。其实我和姐姐也走不动了,埋到脚脖子的沙土已经耗尽了我们所有的力气。我们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停下来。那是一棵高大的树,枝杈辽远地伸向天空。我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树顶,这还是到人家屋后偷吃桑葚练就的功夫。在那个年代,好像所有的男孩都会爬树。我手搭凉棚向远处瞭望。我看到母亲骑自行车的身影,这时我从树上跳了下来。我跳进厚厚的沙土里,它的柔软令我惊异。我没想到泥土会像棉被那样柔软,充满温情,让人迷恋。接着,我又爬上树。我爬上树,只是为了纵身跳下,扑向泥土的怀抱。
我也很怀念铺上沙砾(夹杂着很多碎文蛤壳)的马路。尤其是在傍晚,马路一片静谧,风从路面掠过,轻柔得好像来自梦境。这时你会听到马路上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伴以猫的温柔叫声。我看到我姥娘踽踽独行的身影出现在我家与厕所(陈希芳家后头)之间的马路上。她每天都来来回回走在这段只有一百多米的马路上。我姥娘的世界多么狭小啊,同时,她的世界又是那样辽阔,那是由她操持的日常生活构成的,它绵延阔大得仿佛永无尽头。
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从我家东山头河里响起的的笃的笃声,那是一位头戴草帽的渔夫踩踏一块木板制造出来的,是对鱼鹰发出的指令。总是冷不丁就有两头弯弯的小船出现在我家东头的河上。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喜欢鱼鹰。它们争先恐后潜进水里,就像潜进扑朔迷离的谜语。然后总有谜底——鱼——被衔上来。渔夫驱使鱼鹰逮鱼,其实就是让它们猜谜。而鱼鹰们总是不负所望。我们是多么喜欢这些猜谜能手啊。同时,我们又对它们充满了怜悯:什么时候它们才能吃上一顿辛辛苦苦捕获的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