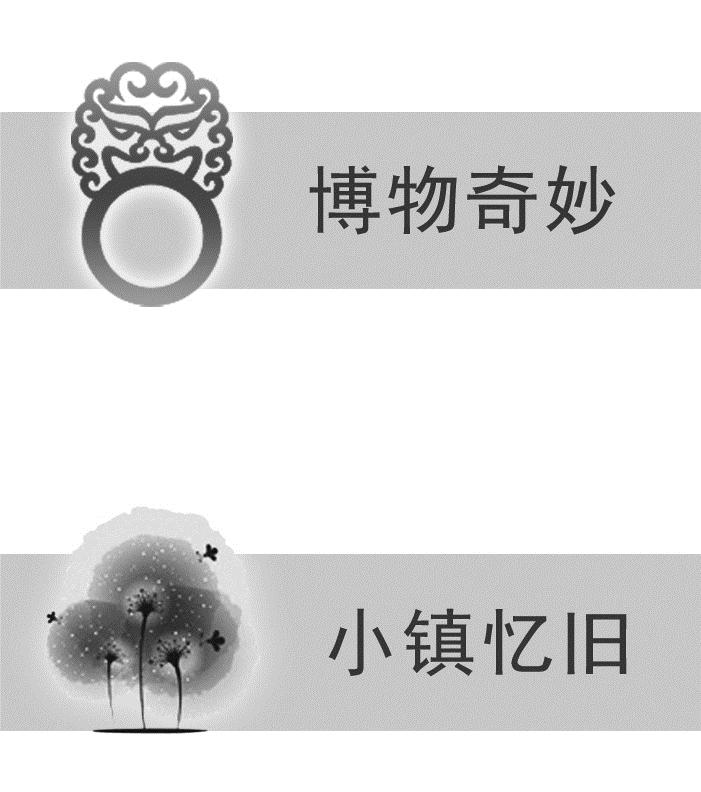□刘剑波
那天早上,我头一次发现我姥娘使用老秤熟练得像个摊贩,她一只手拎起老秤,一只手捋动悬挂秤砣的细麻绳,我甚至能听到细麻绳在秤杆上滑动的细微声响。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厨房门后就挂着一根老秤。跟它挂在一起的,还有用细麻绳系着的秤砣。为了这根老秤,我姥娘没少受累过。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孩子根本没有玩具,我和弟弟就拿秤杆当马骑。我们把秤杆置于胯下,在院子里“得得得”地来回跑着。我姥娘颤巍巍地跟在后面,一遍遍哀求,“行行好,别把秤杆弄断了”。我和弟弟嫌她絮叨,就去马路上“骑马”了,反正我姥娘的小脚又撵不上我们。我和弟弟轮流着往南骑。我们的“马”得意洋洋地跑过陆炳龙家的西山头,继续往南,一直跑到军民桥。从军民桥左拐向东就是“东海部队”了,所以我们又策“马”奔向“东海部队”。等我们返回到家里,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了。急得六神无主、满头大汗的姥娘一把抢走秤杆,察看有没有哪儿损坏。幸亏秤梢头包着铜皮,在地面摩擦得铮亮可鉴。我姥娘让我们骑扫帚,说扫帚更像马。我们哪里肯听,我们只骑秤杆。我们跟秤杆较上劲儿了。我们哪里知道,每当我们把秤杆骑出去,我姥娘是怎样的提心吊胆,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更不理解我姥娘为何爱惜那杆老秤。
再说说秤砣。有一阵子,一只野猫频频光顾我家院子,偷吃猫碗里的食物。我和弟弟伺机躲在暗处,用砖块砸它。我们发现,再没有比秤砣作为投掷物更顺手的了。那只野猫也跟我家的猫碗较上劲儿了,尽管我们一次次砸它,它还是一次次来,这是因为我们一次也没砸中它,尽管秤砣用起来顺手。有一次,那只野猫朝黄豆地逃窜,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秤砣砸到黄豆地里去了。我家南隔壁是曹木匠家,后来曹木匠搬走了,宅地上长了黄豆。那片黄豆地很是茂密,我姥娘俯身一根根黄豆棵子拨弄过去,总算找到了秤砣。我姥娘累得坐在黄豆地里,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尽管我们那么顽皮,不听话,由着性子来,我姥娘从不会呵斥我们,更不会动粗,她总是跟在我们屁股后面,不停地哀求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一个孩子是什么时候长大的呢?当这个孩子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时,就说明他长大了。有天早上,我从床上爬起来,发现我姥娘在院子里用老秤称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果蔬和文蛤。后来我知道这是我姥娘在给买回来的东西复秤。我姥娘的这个举动并不是那天早上才有的,而是早就开始了,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只是被我忽略了。在我们居住在小镇的漫长时光里,都是我姥娘买菜。我姥娘起得很早,当我们还在酣睡时,她就起来了。我们睡醒了,她已经把菜买回来了。那天早上,我头一次发现我姥娘使用老秤熟练得像个摊贩,她一只手拎起老秤,一只手捋动悬挂秤砣的细麻绳,我甚至能听到细麻绳在秤杆上滑动的细微声响。一般情况下,我姥娘对复秤的结果是较为满意的,接着她会收起秤,开始忙早上的一大摊子事。不过,要是那些买回来的东西缺斤少两,根本逃不过我姥娘手中这根老秤。我姥娘会拎起东西,跑到街上去找小贩,高声大嗓与其理论。我姥娘说的是山东方言,对方根本听不懂,旁边有人主动做翻译。对方被我姥娘气汹汹的样子吓坏了,乖乖补齐缺少的斤两。那些坐地贩子不想再找麻烦,只要我姥娘来买东西,会将斤两秤得很足,秤杆恨不得翘到天上去。刁钻的是那些路过的卖瓜买文蛤的流动小贩,待我姥娘回家复秤发觉短了斤两,那些小贩早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我姥娘只好悻悻而回,愤愤不平地说,南方人真坏。
有一次我姥娘对我说,俺来教你称秤。我从不认为那根老秤将来会跟我发生关系,出于无聊我同意了,姑且作为玩儿吧。我貌似很郑重地接过那根秤,我看到秤杆上银灰色的刻度已经斑驳,奇怪,我和弟弟无数次拿它作马骑,怎么就没发觉呢?很显然,刻度的斑驳是我姥娘手掌与手指曾摩挲过它无数遍造成的,它印记着我姥娘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所有时光。我现在还清晰记得我姥娘教我如何使用秤的情景:哪只手拎起杆秤,哪只手捋动悬挂秤砣的细麻绳,如何辨识刻度——秤重的东西和秤轻的东西,它们显示的含义不一样。而且,秤重的东西时要拎秤头外端的那根细绳,秤轻的东西时,要拎秤头稍里面的细绳。尽管我并不知道我正儿八经使用杆秤的时刻正在悄悄逼近,但我却对用秤称东西有了兴趣。我称砖头,称小凳,称水桶,还把米坛里的米舀到米袋里称。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其实在进行操练呢,过不了几年我就以一个小贩的身份用上它。有一次,我突发奇想:称称家里的小猫小狗。猫很狡猾,总是在最后时刻逃得无影无踪。狗倒很配合,老老实实待在网兜里,可怜巴巴地盯着我,以为我会卖了它。
上初中时我开始跟着邻居信发下海了。陆善堂有四个儿子,信发是幺儿,人们叫他小四。小四比我年长几岁,已经是“老海货”了。每次下海都挑一担文蛤回来。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的我却很惨,几斤文蛤装在网兜背在背上,简直是无地自容。后来有了经验,手脚也变快了,收获物随之增多,居然也能重担在肩了。每次“哎哟哎哟”挑回文蛤,父亲总要拣两斤最大的家里吃,剩下的大头就得卖掉了。那年头文蛤真是多,街上铺天盖地都是文蛤,八鲜行里的文蛤都堆成了山,陆善堂们正忙着往李堡送。我突然醒悟过来:几年前进行称秤的操练,就是为这个时候做准备的——多么神奇的造物啊。我挑着文蛤出门时,我姥娘把那根老秤塞给了我。谁能想到呢,一根本来与我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件,竟然走进了我生命。
就这样,我肩挑文蛤手持老秤来到了街上,那儿早已摆了一长溜文蛤。我找了个空地儿,搁下文蛤的那一瞬间,命运让我成了一名年轻的小贩,年轻得让人心疼。我不好意思吆喝,身边的人都“卖文蛤”喊成了一条声。多年后我看郭达《卖大米》的小品,笑得差点岔过气去。不过,还是有人买我的文蛤。我
一只手拎起杆秤,一只手捋动悬挂秤砣的细麻绳,虽然周围喧嚣不堪,但我仍能听到细麻绳在秤杆上滑动的细微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