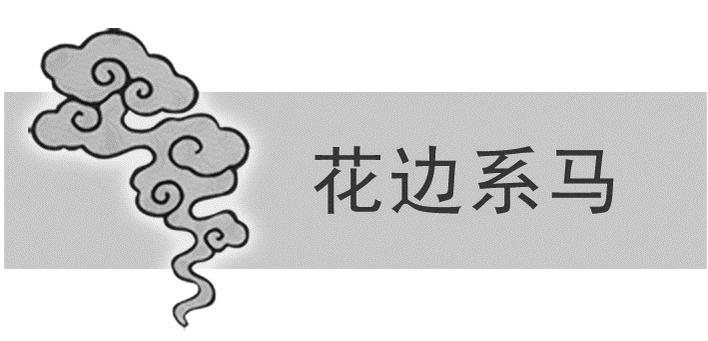□王春鸣
在两仪四象的时空里,我们最后只能借几根菖蒲艾蒿,来重建和自然的联系,有点失落,也有点庆幸。
菜市场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去处,倒也不是因为会做菜,而是因为走在买菜往返的陌生人群里,有一种被人间烟火拥抱的踏实。高山大海当然也能修补人生,但是遍布在日常岁月里的小小的罅隙、不平的心绪,还是要这平凡之至的饭菜蔬食、熙熙攘攘的市声,来穿针引线缝缝补补。
尽管反季食品肆虐,在菜场,还是能非常分明地看到四季物候的变化。毛豆、襄荷、莲蓬上市,煮好的咸鸭蛋被敲开来,蛋黄红油汹涌,而红苋菜已经老了……是的这就又到了端午,端午,我一直觉得它是节气,也一直疑惑它自然气息如此浓郁,怎么竟不是节气。年年此刻,袁灶的院墙下,爸爸手植的艾蒿成片招展,妈妈也去河边采来芦叶,包好了赤豆白米粽。我还记得去年,爸爸喊我割几根艾蒿,我在地头捡起一只黑壳子小虫,它是凉的,可是我把它放在艾叶上,它却纵身一跃,钻到旁边的菜地里去了。
但是今年,一切都不一样了。
早起读了几篇归有光的散文,忽然怅惘,无可排解,就去了菜场。一个老人慢吞吞与我擦肩而过,他一手拎翠绿香瓜,一手握满把菖蒲艾蒿,颇有点像从陆游《浣溪沙》里走出来的人物。而其他各种迎面而来的自行车、电瓶车、小拖车上,也都摇曳着一把把青翠的蒲艾,原本空气里弥漫的米面早点味儿,都被它们清苦的香气覆盖了。
我去买昨天才买过的黄色小番茄,那家八卦洲农民菜的摊位上,所有的蔬菜瓜果都特别好吃,小番茄价格只有盒马超市的三分之一,但是里面的阳光、水分、春风和甜,几乎要满溢出来。这家摊位和他旁边蔬菜摊位今天都兼卖蒲艾了,两元一把,五元三把,于是几乎所有买菜人的手上,都有菜有肉又有蒲艾。“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我有点吃惊,发现自己无意中从镇江路菜场这个平平无奇的通道,进入了一个民间的盛大的节日。
拎着小番茄和两把蒲艾走在人群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却又如此安心。《本草纲目》说艾草“温中、逐冷、除湿”,果然如此。何况卖艾草的人告诉我,这是她今天清晨踩着露水割下来的,而搭配在一起的菖蒲叶子也是我喜欢的,这传说中的灵草,另有一种奇香。它们都不好看,不凭叶子,不凭花朵,不凭果实,就凭一缕香气包罗了万象。
年少时也曾喜欢热烈的甜香:夏季正午的玫瑰、雨中的栀子、一百朵茉莉同时盛开……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清苦的味道更得我心了,清苦二字,不管发音还是意思,都让人感到沉迷和惘然,像是天阴了却又迟迟不下雨,像是约好了踏青又不能成行,像是什么还没做,日头就过了午。
香味是只能闻闻的,我做过艾草团子,三月鲜嫩的艾草和糯米粉调和,包上绿豆蓉的馅儿,再小火蒸熟。有时也采鲜嫩的艾草叶芽,汆水后凉拌,都不太好吃,它的香味并不适合入口。
一年有很多节日,在所有的节日里,之所以钟情端午,是因为只有它,像节气一样,和许多植物有关,芦苇、蒲草、艾蒿……这是宇宙自然的三百六十五天当中唯一一段用香气写成的履历,从这一点来说,它和屈原,热爱白芷麋芜的屈原,是真的很般配。
发明端午的古人关注到了自然,然后用它最美的部分一样样提醒自己,如何祛魅排毒,如何安身立命。于是,各种仪式就形成了。
东方人都喜欢端午,据说在飞鸟时代,日本也过起了端午节,他们吃用槲树叶包的柏叶饼,用竹叶包的米粉粽子,也插菖蒲,把五月五日叫做菖蒲之节。后来不知怎么又把它变成了儿童节,这也非常好,儿童叫人想起初夏,想起新生的叶子。
端午这个日子,在芒种和夏至之间,好像是割麦种稻之间的一次喘息、歇气。在两仪四象的时空里,我们最后只能借几根菖蒲艾蒿,来重建和自然的联系,有点失落,也有点庆幸。我把用红纸包着的蒲艾散开,插在阳台上的坛子里,而我自己,一只只吃着小番茄,看它们微卷起叶子,像一首时间的诗,慢慢浮现在寂静的音节里,它传来立春的声音,清明的声音,小满的声音,还有古人吟诗的声音: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