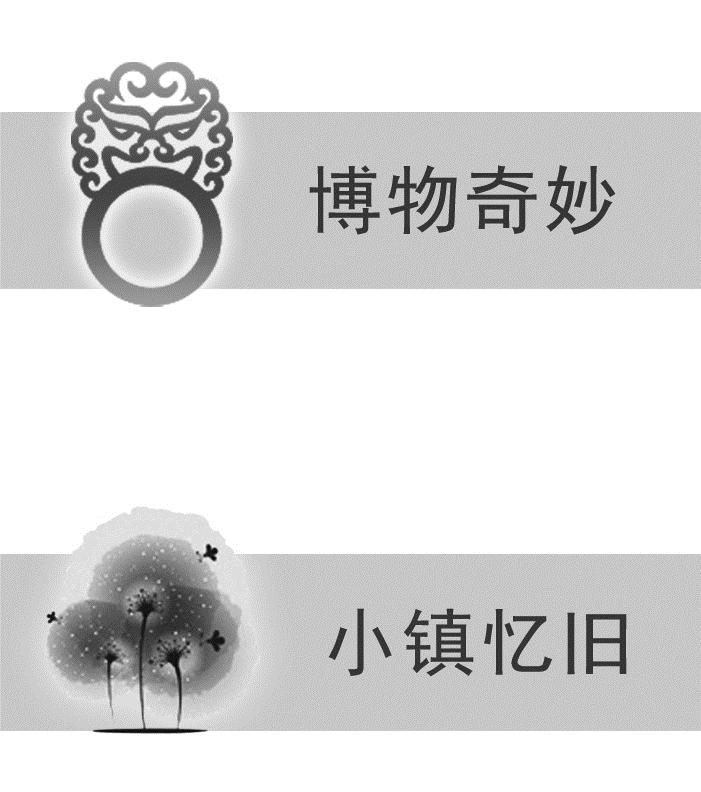“远方”是孩子们心里的一幅美妙图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这幅图画添色加彩。“生活在别处”就是在这个时候于他们心田萌芽的。
□刘剑波
小时候,远方总是强烈地吸引我。或者说,召唤。远方会召唤所有的小孩子。没有哪个小孩子能摆脱得了远方的诱惑。这或许可以叫做“远方情结”,这情结会一直陪伴着孩子的成长。“远方”吸引我们这些孩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远方充满了神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远方”成了神秘的代名词。远方是一个悬在孩子们头上的巨大谜语,孩子总是渴望通过行走抵达的方式找到谜底。二是,孩子们将很多美好的想象赋予了“远方”。“远方”是孩子们心里的一幅美妙图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这幅图画添色加彩。“生活在别处”就是在这个时候于他们心田萌芽的。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生活在别处”的念头会越来越强大。它其实是一种情怀,尽管它很虚幻,但正因为虚幻才显得有美感。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远方”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认为只要与我居住的小镇拉开了距离的地方就是“远方”,比如北坎,比如卫海,比如苴镇,再比如掘港,而南通是绝对不敢想象的,我们甚至都没听说“南通”这个地方。不过“北京”倒是耳熟能详,因为我们天天听小朋友在收音机里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听李双江的《北京颂歌》更是让我热血沸腾。我正是通过歌声认识北京的,在睡梦里,我总是乘着歌声飞到遥远的北京。那时有本歌曲集叫《战地新歌》,后来还出了续集。《北京颂歌》就收在里面。后来我学会了拉二胡,会拉的头一首曲子就是《北京颂歌》。我到现在还是李双江的铁粉。前几天我在网上的一个视频里看到了李双江,他已经老了,可是谁能敌得过时间呢?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啊。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我跟着母亲去两公里外的一个远房表兄家吃喜酒回家的情景。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去“远方”。回来的路上,月光在河面上闪耀,后来乌云遮住了月亮,河面变得很黑,树也是黑的。后来月亮露出了面庞,月光反射在田野上,看起来就像绸缎一样光滑。那些被雪覆盖的房子就像睡着了的蜷成一团的小白熊。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想象自己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我觉得我可以听见羊群在薄雾中发出的甜美鼾声,我觉得我能看到狼站在田埂上,它们的眼睛就像河水一样闪闪发亮。等我们终于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从我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月光依然在闪耀——在水面上,在我家院墙上,在我窗户前的柳树上。
我还记得我6岁时跟姐姐去卫海的旅程,那是我第一次去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卫海离我住的小镇有七八公里,我背着一把玩具枪,那是燠热的夏天,宛若火盆的太阳炙烤着我们。还没跑到陆河,我们就累瘫了。但是对卫海的美好想象支撑着我们。我们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才到达卫海。卫海算不上一个小镇,一些商店及医院和粮站分散在马路两侧,根本不及我居住的小镇,但我还是满心欢喜,因为我毕竟来到了“远方”。我和姐姐去找在卫海医院当院长的父亲,领我们去的是杨医生。杨医生长得高大魁梧,他们都叫他杨大麻子,但我不觉得他麻。那天下午,杨医生送我和姐姐回家。我坐在前车杠上,姐姐坐在后座上。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杨医生抱我去镇上的花部看电影。他在我家住了几天。后来父亲告诉我,杨医生肚子大,吃不饱,故留他几天。去年我在同业苑碰到杨医生,他来女儿家小住。他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我问他,还记得从前抱我看电影的事吗?他脸上一片茫然表情。我并不觉得奇怪。时间带走了我们身体的同时,也带走了多少记忆啊。
我是和几个小伙伴是推着铁圈去北坎的。北坎也是一个小镇,在我居住的小镇东南,路程比卫海稍远。北坎没有让我失望,它是个安静的小镇,街道成丁字形,商铺排列有序,市井气息浓郁。我们赶到那儿时,正碰到饮食店的肉包落笼,从白雾般的蒸汽中飘出来的香味把我们击垮了。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只要能吃上一口,让我们死也心甘情愿。我们凑钱买了两只热乎乎的包子。五个孩子轮流着吃,你咬一口,我咬一口。我们都责怪对方嘴张得太大,咬得太多了,吵吵嚷嚷闹成一团。有个小伙伴最后衔着半个包子逃走了。我们在后面拼命追赶。当我们好不容易追上,那半个包子已经下肚。不记得我们有没有揍他一顿,反正我们都沮丧极了。
再往后,我学会了骑车,所以,去苴镇是骑自行车去的。我个子矮,只能骑车杠。这实际上很痛苦,你的屁股要不停地在车杠上方来回运动,一旦你偷懒停下来,自行车也停下来了。在我看来,苴镇作为一个区级镇,是个大地方,能去一趟苴镇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回来后,我跟小伙伴们聊苴镇足足聊了三天。但是,如果能去一趟掘港呢?跟苴镇比,掘港简直就是天堂,镇上的一群孩子里,谁都没有去过掘港。那时我甚至想,我这辈子的最大的事就是去一趟掘港。有一天,母亲把她收拾得干净锃亮的女式自行车从屋里推出来。母亲说,她要去掘港办事。听母亲这么说,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我缠住母亲,让她带我去。但是母亲拒绝了,母亲是个执拗的人,无论我怎么央求,她始终不松口。最后的时刻来临了,母亲把自行车从院子推到马路上,又推着疾走了几步,然后跨上去。可是她发现推不动了,我已经牢牢拖住了。母亲急坏了,让我松手。我抱定主意,除非把我手砍了我才松手。这时,从南边跑过来的陆炳龙帮了个忙,他稍一用力,就把我的手从衣包架上掰下来了。他紧紧抱住我,让我动弹不得,我眼睁睁看着母亲骑着车渐行渐远。我低头在陆炳龙手腕上狠狠咬了一口,我可能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陆炳龙疼得哇地大叫了一声,把我扔在地上。我爬起来去追母亲。哪里追得上,母亲早已从我视线消失了。那天,很多人都听到了我绝望的哭声。也有人说我并没有哭,说我一直在呼喊着母亲。他们说,那是远方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