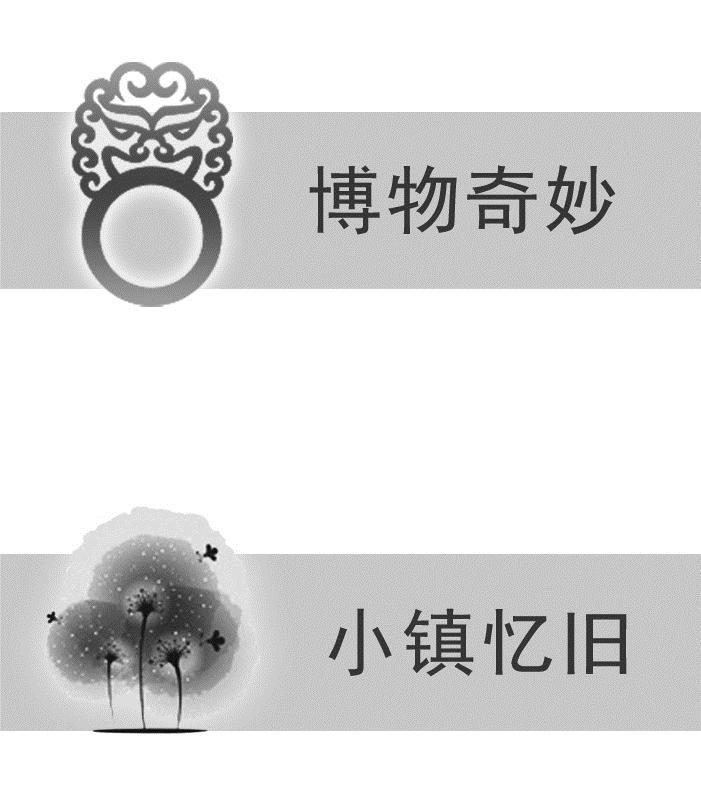他稳操胜券的样子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捏在他手里。我还看到过他跑步的样子。那时他也是很专注,眼睛看向远方,脚步有板有眼地在马路上划动。
□刘剑波
每当回忆小镇的人和物,我耳边会无法避免地响起郭新明“一二一”的喊声,那是他在马路上跑步。他在对自己沉重又轻盈的步履发出口令。它高亢,苍凉,决绝。它悠长,深情,固执。但后来我觉得那声音可能是郭新明对脚下的马路发出的叩问和责难。有时我脑子里还会浮现这样的念头:那声音也许是郭新明对脚下的马路进行晨祷的呼唤,他是多么希望马路能拯救他啊,他是多么希望马路能把他带到远方去啊。我经常想,马路仅仅是马路吗?马路会不会是一种隐喻?马路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余华曾经将马路比作绳索,但我更愿意把马路比作脐带。我觉得人类到现在也没有将自己的脐带剪断,脐带一直捆缚着人类。我们都被脐带捆缚得奄奄一息,所以郭新明才会以跑步的方式,让自己获得救赎。他在用脚步摆脱脐带的捆缚。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新明简直就是先知。
然而,只要一提到郭新明,小镇人都会以不屑和嘲弄的口吻说,那个郭呆子啊!在我们这个小镇,不仅大人叫他郭呆子,连毛头小孩也叫他郭呆子。他的名字都被人们淡忘了。穿过雾霭重重的锈蚀岁月,我能清晰地看到郭新明伫立在小镇街头,眼神迷茫地四处张望。他中等身材,永远穿着一件浅色褂子。太阳照着他饱满的大额头,你能看到他的大额头闪耀着光泽。因为光线太强,他的眼睛眯缝起来。后来我发现,并不是因为光线他才会把眼睛眯缝起来。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平时就是眯缝着眼打量着你,好像在说“你别装,我什么都知道”。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这种打量下变得心慌,无地自容,最终败下阵来。要是你留心观察,你会发觉他的眼睛里有种灵光乍现的东西,你会惊奇愕然,不知所措。你还会发觉他的眼神单纯,素朴,纯净,让你无法跟他对视。
小镇人叫他郭呆子,可能是因为一年四季,无论起风还是下雨,他都要在马路上跑步。他简直成了计时的沙漏。小镇人会从他渐行渐近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判断几点钟了。小镇人叫他郭呆子,还因为他神色恍惚,疯疯癫癫,有时候自言自语,有时候骂骂咧咧,有时候兀自大笑,有时候面露凶相,人们唯恐避之不及,有时候神情善良,面色温和,即便当面叫他郭呆子,他也会笑嘻嘻的,跟你握手,老半天也不松开。有时我会觉得,这符合先知的特征。先知就是这个样子的。而更多的时候,“呆子”这个词会让我困惑,在这个世界上,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呆子”呢?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呆子”吗?“呆子”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呆子”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跟我们不生活在一个维度,他们置身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所以在我们看来,他们特立独行,做出我们看不惯的不符合常理的怪异举动。然而,他们怎么看我们呢?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才是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和他们彼此照出了自己。我们和他们组成了人类的整体,我们是孪生的,我们相依为命,我们不可分割。所以,请不要叫他们“呆子”,当你叫他们“呆子”时,说不定你自己就是“呆子”呢?
小镇人都说郭新明是因为读书读多了才呆的,所以,小镇酷爱读书的孩子都会被大人严重警告:当心,别变成郭新明啊。少年时代的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书读多了会变呆。当然,那个时代根本无书可读,我所说的“读多了”是指对一本书无数次地读,比如那本“老虎皮”,我读了N遍,是它诱发了我对武术的爱好,并对武松的铁布衫功心驰神往。我和同学吴敦圣频频拜访据说武艺高强的王侉儿。但王侉儿总是做出一副秘不示人的神情,他让我和吴敦圣做得最多的,就是到街头去捡香烟头,他再用烟头制作香烟,并许下愿来,要是捡了多少多少烟头,就教我们几招,这使我们欣喜若狂。我们来来回回在街上逡巡,我们的眼睛紧紧盯着地面,只要一瞄到烟头就抢奔过去。有时,我们实在找不到烟头了,就站在吸烟的人身旁等候,我们用贪婪的眼睛催促着他:快吸啊,您倒是快吸啊,我们在等着您的烟头呢。在我们眼里,那哪是烟头啊,那简直就是下锅的米。可是王侉儿总是食言,当我们达到了他的要求,他又说再捡多少多少烟头,保证教我们。结果他还是没有教我们。
只有在郭新明跟“麻木队长”下棋的时候,小镇人才不会叫郭新明郭呆子。我看到过他跟“麻木队长”对弈。他神情专注,他眼睛里充满了睿智。他稳操胜券的样子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捏在他手里。我还看到过他跑步的样子。那时他也是很专注,眼睛看向远方,脚步有板有眼地在马路上划动。啊,马路,他心里会这样一遍遍地自言自语。他跑步的路线,通常是从小镇东街口沿马路向南到“东海部队”,然后再折返跑回小镇,擦过车站往西,跑向卫海方向。我知道他其实在用脚步挣脱马路,他对马路又爱又恨。马路是他的梦魇,马路也是他的期冀。当他经过我家西山头时,他会看到我姥娘在生煤球炉。我姥娘喜欢在马路边上生炉子,因为马路上空旷风大。郭新明总是叫我姥娘“大娘”,他的话音里有种南腔北调的东西,让我着迷。整个小镇,除了郭新明,还有卖猪肉的季星山也叫我姥娘“大娘”。我很喜欢他们。我对他们有种天然的亲切感,这是因为他们叫我姥娘“大娘”的缘故。我有时会恍惚觉得,他们两个哪里是小镇上的啊,他们分明就是我姥娘老家的人,那个坐落在高密柴沟土庄的小村子里的人,那个小村子叫王家大庄。
很多时候,郭新明也会在下午跑步。那是在夏天,我们这些孩子在我家东山头的那条河里游泳。这时有机器船“通通通”地开过来。我们游过去抓着船沿,我们被船拖着顺流而下。我们多么希望顺流而下漂向远方啊……
我很怀念郭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