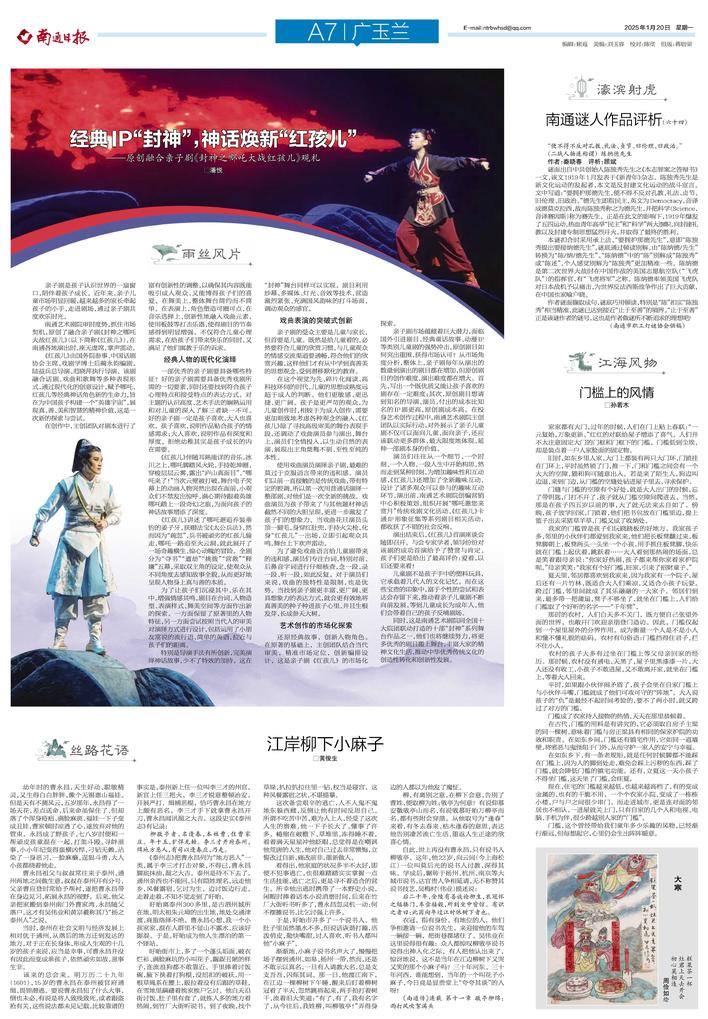□黄俊生
幼年时的曹永昌,天生好动、聪敏精灵,又生得白白胖胖,像个无锡惠山福娃。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五岁那年,永昌得了一场天花,差点送命,后来命虽保住了,但却落了个浑身疮疤、满脸麻斑,福娃一下子变成丑娃,曹家顿时凉透了心,遂放弃对他的管束。永昌成了野孩子,七八岁时便和一帮顽皮孩童混在一起,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小小年纪变得蛮横凶悍,刁钻无赖,沾染了一身恶习,一脸麻癞,逞狠斗勇,大人小孩都绕着他走。
曹永昌祖父与叔叔常往来于泰州、通州两地之间做生意,叔叔在泰州开有分号,父亲曹应登时常给予帮衬,遂把曹永昌带在身边见习,拓展永昌的视野。后来,他父亲把家搬到泰州南门外曹家湾,永昌随父落户,这才有吴伟业和黄宗羲称其乃“扬之泰州人”之说。
当时,泰州在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上相对优于通州,从落后的地方迁到发达的地方,对于正在长身体、形成人生观的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应当是幸事,可曹永昌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乖孩子,依然顽劣如故,滋事生非。
该来的总会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15岁的曹永昌在泰州被官府通缉,畏罪潜逃。要说曹永昌犯了什么大事,倒也未必,有说是将人致残致死,或者跟盗抢有关,这些说法都未见记载,比较靠谱的事实是,泰州新上任一位叫李三才的州官,新官上任三把火,李三才锐意整顿治安,开展严打,缉捕恶棍,恰巧曹永昌在地方上颇有恶名,李三才手下就拿曹永昌开刀,曹永昌闻讯溜之大吉。这段史实《泰州志》有记录:
柳敬亭者,名逢春,本姓曹,住曹家庄。年十五,犷悍无赖。李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恶人,有司以逢春应,乃走。
《泰州志》把曹永昌列为“地方恶人”一类,属于李三才打击对象,不得已,曹永昌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泰州是待不下去了,通州余西也不能回,只有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风餐露宿,乞讨为生。边讨饭边行走,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盱眙。
盱眙离泰州300多里,是古泗州城所在地,明太祖朱元璋的出生地,地处交通津渡,商旅络绎不绝。曹永昌心想,我一个小孩家家,混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应该好厮混。于是,盱眙成为他人生漂泊的第一个驿站。
盱眙街市上,多了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满脸麻坑的小叫花子,龌龊丑陋的样子,连流浪狗都不敢靠近。手里捧着讨饭碗,腋下挟着打狗棍,没纽扣的破袄,用一根草绳系在腰上,趿拉着没有后跟的草鞋,在雪地里蹒跚着挨家挨户乞讨。他白天沿街讨饭,肚子里有食了,就拣人多的地方看热闹,到竹厂大街听说书。到了夜晚,找个草垛,扒拉扒拉往里一钻,权当是寝宫。这种风餐露宿之状,不堪描摹。
这次备尝艰辛的逃亡,人不人鬼不鬼地东躲西藏,反倒让他有时间反思自己。所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经受了这次人生的磨难,他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许多。蜷缩在破檐下、草堆里,冻得睡不着,看着满天星星冲他眨眼,总觉得是在嘲讽他荒唐的人生,他对自己过去非常懊悔,立誓改过自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看得出,他家庭的状况多半不太好,即便不犯事逃亡,也很难踏踏实实掌握一点生活技能,逃亡之后,更是寻不着适合的营生。所幸他出逃时携带了一本野史小说,闲暇时捧着话本小说消磨时间,后来在竹厂大街听书听多了,曹永昌忽灵机一动:何不摆摊说书,比乞讨强上许多。
于是,盱眙市井多了一个说书人。他肚子里虽然墨水不多,但说话诙谐打趣,活泼俏皮,勤快嘴甜,讨人喜欢,听书人都叫他“小麻子”。
渐渐地,小麻子说书名声大了,慢慢把场子摆到通州、如皋、扬州一带,然而,还是不敢示以真名,一旦有人请教大名,总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那一日,他渡江南下,在江边一棵柳树下午睡,醒来后盯着柳树冠看了半天,忽然跳将起来,两手拍打着树干,流着泪大笑道:“有了,有了,我有名字了,从今往后,我姓柳,叫柳敬亭!”弄得身边的人都以为他发了魔怔。
柳,有离别之意,在柳下会意,告别了曹姓,便取柳为姓;敬亭为何意?有说仰慕安徽敬亭山而名,有说敬慕盱眙万柳亭而名,都有些附会穿凿。从他取号为“逢春”来看,有冬去春来、枯木逢春的意思,表达他告别凄苦流亡生活、重返人生正途的欣喜心情。
自此,世上再没有曹永昌,只有说书人柳敬亭。这年,他22岁,向云间(今上海松江)一位叫莫后光的说书人讨教,深得其味。学成后,辗转于扬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说书,达官贵人争相延请,无不称赞其说书技艺,吴梅村(伟业)描述说:
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门,车尝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曰:此固向年过江时休树下者也。
衣冠,指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争相邀请一位说书先生,来迎接他的车驾一辆接一辆,把街巷都堵住了。吴伟业在这里说得很有趣:众人都惊叹柳敬亭说书说得出神入化之际,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惊讶地说,这不是当年在江边柳树下又哭又笑的那个小麻子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想到,当年的一个叫花子小麻子,今日竟是显贵堂上“夸夸其谈”的人呀!
《南通传》连载 第十一章 敬亭柳绵:雨打风吹絮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