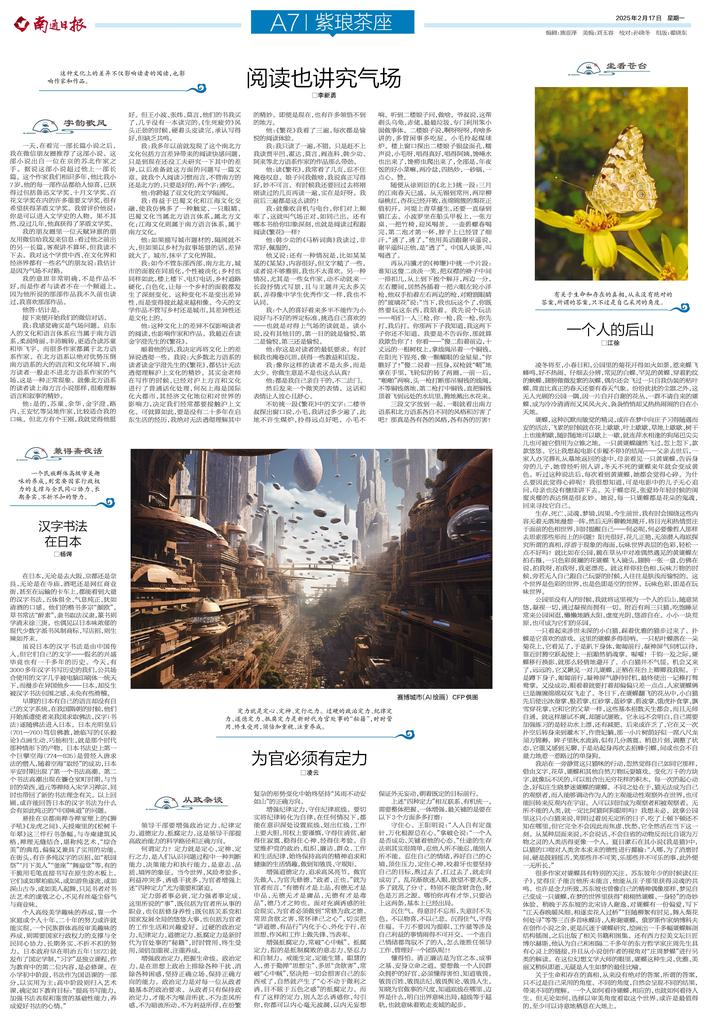□李新勇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影响读者的阅读,也影响作家和作品。
一天,在看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我在微信朋友圈推荐了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出自一位在京的苏北作家之手。据说这部小说超过他上一部长篇。这个作家我们相识多年,他比我小7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人惊喜,已获得过包括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在内的许多重要文学奖,很有希望获得茅盾文学奖。我曾评价他说:你是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人物。果不其然,没过几年,他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我的朋友圈里一位天赋异禀的朋友用微信给我发来信息:看过他之前出的另一长篇,客观讲不算坏,但我读不下去。我对这个学贯中西、在文化界和经济界都有一些名气的朋友说:我估计是因为气场不对路。
我的意思非常明确,不是作品不好,而是作者与读者不在一个频道上。因为他所说的那部作品我不久前也读过,我喜欢那部作品。
他答:估计是。
接下来便开始我们的微信对话。
我:我感觉确实是气场问题。启东人的文化和语言体系应当属于南方语系,柔润绮丽、丰沛婉转,更适合读苏童和毕飞宇。而很多作家都属于北方语系作家。在北方语系以绝对优势压倒南方语系的大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下,南方读者一般走不进北方语系作家的气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就像北方语系的读者读上海方言小说那样,很难理解语言和叙事的精妙。
他:是的,苏童、余华、金宇澄、路内、王安忆等吴地作家,比较适合我的口味。但北方有个王刚,我就觉得他挺好。但王小波、张炜、莫言,他们的书我买了,几乎没有一本读完的。《生死疲劳》风头正劲的时候,硬着头皮读完,承认写得好,但缺乏共鸣。
我:我多年以前就发现了这个南北方文化包括方言差异带来的阅读快感问题,只是到现在还没工夫研究一下其中的差异,以后准备就这方面的问题写一篇文章。就我个人阅读习惯而言,不管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只要是好的,两个字:通吃。
他:你跨越了亚文化的文学隔阂。
我:得益于巴蜀文化和江海文化交融,使我仿佛多了一种触觉、一只眼睛。巴蜀文化当属北方语言体系,属北方文化;江海文化则属于南方语言体系,属于南方文化。
他:如果描写城市题材的,隔阂就不大,但如果以乡村为叙事场景的话,差异就大了。城市,抹平了文化界限。
我:如今不管东部西部、南方北方,城市的面貌在同质化,个性被淡化;乡村也同样如此,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乡村道路硬化、白色化,让每一个乡村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变出差异性,而是变得彼此越来越相像。今天的文学作品不管写乡村还是城市,其差异性还是文化上的。
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影响读者的阅读,也影响作家和作品。我最近在读金宇澄先生的《繁花》。
顺着他的话,我决定再将文化上的差异说透彻一些。我说:大多数北方语系的读者读金宇澄先生的《繁花》,都估计无法透彻理解沪上文化的精妙。其实金老师在写作的时候,已经对沪上方言和文化进行了普通话化处理,何况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其经济文化地位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决定我们经常都要接触沪上文化。可就算如此,要是没有二十多年在启东生活的经历,我绝对无法透彻理解其中的精妙。即便是现在,也有许多领悟不到的地方。
他:《繁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是愉悦的阅读体验。
我:我只读了一遍,不错。只是赶不上我读贾平凹、霍达、莫言、阎连科、韩少功、阿来等北方语系作家的作品那么带劲。
他:读《繁花》,我常看了几页,忍不住掩卷叹息。娘子问我做啥,我说真正写得好,妙不可言。有时候我还要回过去将刚刚读过的几页再读一遍,实在是好呀。我前后三遍都是这么读的!
我:就像收音机与电台,你们对上频率了,这就叫气场正对、如同己出。还有哪本书给你印象深刻,也就是阅读过程跟阅读《繁花》一样?
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我读过,非常好,佩服的。
他又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某某某的《某某》,内容很好,但文字糙了一些,或者说不够雅驯,我也不太喜欢。另一种情况,尤其是一些女作家,动不动就来一长段抒情式写景,且与主题并无太多关联,弄得像中学生优秀作文一样,我也不认同。
我:个人的喜好看来多半不能作为小说好与不好的界定标准,挑选自己喜欢的——也就是对得上气场的读就是。读小说,没有其他目的,第一目的就是愉悦,第二是愉悦,第三还是愉悦。
他:你这是对读者的最低要求。有时候我也掩卷沉思,获得一些教益和启发。
我:像你这样的读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你做生意是不是也这么认真?
他:都是我自己亲自干的,不二法门。
然后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这话和表情让人放心且舒心。
不妨挑一段《繁花》中的文字:二楼爷叔探出窗口说,小毛,我讲过多少遍了,此地不许生煤炉,拎得远点好吧。小毛不响。听到二楼娘子问,做啥。爷叔说,这帮剃头乌龟,赤佬,最最垃圾,专门利用笨小囡做事体。二楼娘子说,啊呀呀呀,有啥多讲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小毛拎起煤球炉。楼上窗口探出二楼娘子银盆面孔,糯声说,小毛呀,唱得真好,唱得阿姨,馋唾水也出来了,馋痨虫爬出来了,全部是,年夜饭的好小菜嘛,两冷盆,四热炒,一砂锅,一点心。赞。
随便从徐则臣的《北上》挑一段:三月的江南春天已盛。从无锡到常州,两岸柳绿桃红,杏花已经开败,连绵锦簇的梨花正值初开。河堤上青草蔓生,还要一直绿到镇江去。小波罗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一壶碧螺春喝完,第二泡才第一杯,脖子上已经冒了细汗。“通了,通了。”他用英语跟谢平遥说。谢平遥纠正他,是“透了”。中国人谈茶,叫喝透了。
再从冯骥才的《神鞭》中挑一个片段:谁知这傻二淡淡一笑,把双襟的褂子中间一排扣儿,从上到下挨个解开,两边一分,左右腰间,居然各插着一把六眼左轮小洋枪,他双手拍着左右两边的枪,对瞪圆眼睛的“玻璃花”说:“当下,我也玩这个了,你既然要玩这东西,我陪着。我先说个玩法——咱们一人三枪,你一枪,我一枪,你先打,我后打。你那两下子我知道,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我要是不告诉你,那就算我欺负你了!你看——”傻二指着前边,十丈远的一根树杈上,拿线绳吊着一个铜钱,在阳光下锃亮,像一颗耀眼的金星星。“你瞧好了!”傻二说着一扭身,双枪就“唰”地拿在手里,飞轮似的转了两圈,一前一后,“啪啪”两响,头一枪打断那吊铜钱的线绳,不等铜钱落地,第二枪打中铜钱,直把铜钱顶着飞到远处的水坑里,腾地溅出水花来。
三段文字放到一起,一眼就看出南方语系和北方语系各自不同的风格和厉害了吧?那真是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