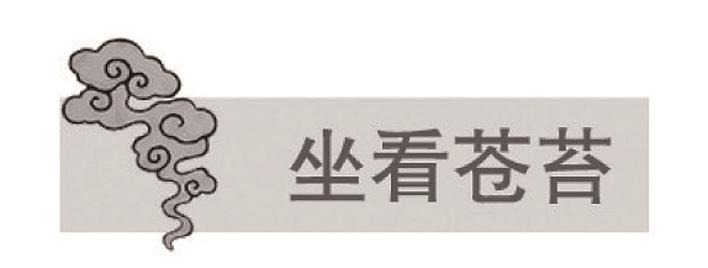□江 徐
四月的清早,我出门走走,就看到了那棵槐树,白色花串儿挂满枝头。这条路之前多次经过,有时经过也会在意到这棵树,一看便知有年代了。这次“看见”它,是因为我在慢慢行走。只要行走,总会有所遇见,哪怕是一条来来回回走过很多遍的寻常路。
树下,门前,老人摆着小摊儿,远远望着像是布料。我过了马路来到摊前,确实是一筐碎布料,有点像蓝印花布。“带一块回去,可以帮小官裁条裙子。”老太太说。我告诉她自己不会裁做衣裳。“这样一裁、一缝,就好了呀。”她边说边做动作,仿佛做一件小孩衣裳也就是三下五除二的事,跟叠纸飞机一般轻巧。见我犹疑,她从脚边塑料袋里掏出件小背心,“喏,现成的,要哇?”小巧,蓝白镂空花纹,几粒大红圆纽扣很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味道。我没小官,买了回去也不过是扔那儿,但这件小衣裳实在惹人喜爱的,很有可能还是老人家开门第一桩生意呢,遂问价。“八块,就两斤茄子的铜钿。”她笑答。她没手机,我没现金,我就去隔壁人家兑换。隔壁那位阿姨也上了年纪,一头银灰头发,取了个微信名字叫“雨天中的晴天”,品玩一番,心中又一悦。
付完钱,拿了衣服,我就站到檐下看槐树,寻找拍摄的最佳角度。人间四月天,槐花如雪,一对凤蝶围着高枝翩翩跹跹颤颤抖抖,欲分槐花香蜜一杯羹。
一位闲人踱了过来,看看我,看看树,问我在拍什么。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我就朝对面的槐树指指。他像不知道这是树似的,问道:“这是啥呀?”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其实也懒得回应时,卖布料的老奶奶接话了:“槐树呀!”闲人依然直愣愣,追问道:“槐树怎么了?”生活中是有这种人的,我相信他是真的不明白,不明白一棵平平无奇的树,有啥好拍的。这一类人,对生活中很多东西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观念对某样东西是从来不在意的。
我站在一旁拍槐树,没有细听,耳朵里刮到一些,老奶奶告诉那位闲人,槐花能吃什么、能治什么,疗效还很不错。闲人对此表示怀疑,说,哦,有这么厉害?由此,老奶奶娓娓道来:“这棵槐树呀,已经有五十多年,还是我三十来岁的时候亲手栽的,栽了好几棵哩,都被弄掉了,就剩下这一棵……”她又说自己有三个儿子,拆迁,分到三套房子,儿子们都表示不要,都愿意把这房子给她和老头子。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房子迟迟还未拿到手。所以,目前老两口依然住在这棵老槐树下,已然破落的老房子里。
老人看起来已进望九之年,还能裁裁剪剪。在路边摆摊时,老伴也在一旁,坐在轮椅上,看起来听力已不行,神情呆滞,脑子估计也不太清晰。
过了几天,我心血来潮想尝试煮一顿槐花饭吃吃,这里槐树很少见,于是特地寻去老奶奶家。才过去一星期左右,也没下过雨,也没刮过风,枝头已不见白花。推开虚掩的铁门走进院子,老奶奶正倚着水池淘米,院内,四壁角落堆着散乱破旧的杂物,长在西南角的一棵银杏已经高出屋顶,绿得沁人心脾。
向她道明来意。她叹息道,没有啦,都被他们弄掉啦。前两天不知从哪来了两个人,带了竹竿来敲槐花,通通敲打了去。我问,这棵槐树不是你家的吗?她说是呀,是我家的,那天我问他们要一点,还不愿意给。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竟然也是有的。
我在院子里站了会儿,四月艳阳天,那棵上了年纪的幸存下来的槐树看起来郁郁葱葱。屋檐上有两棵瓦松,不知何时吹来的草籽,在这个角落静静生长,一岁一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