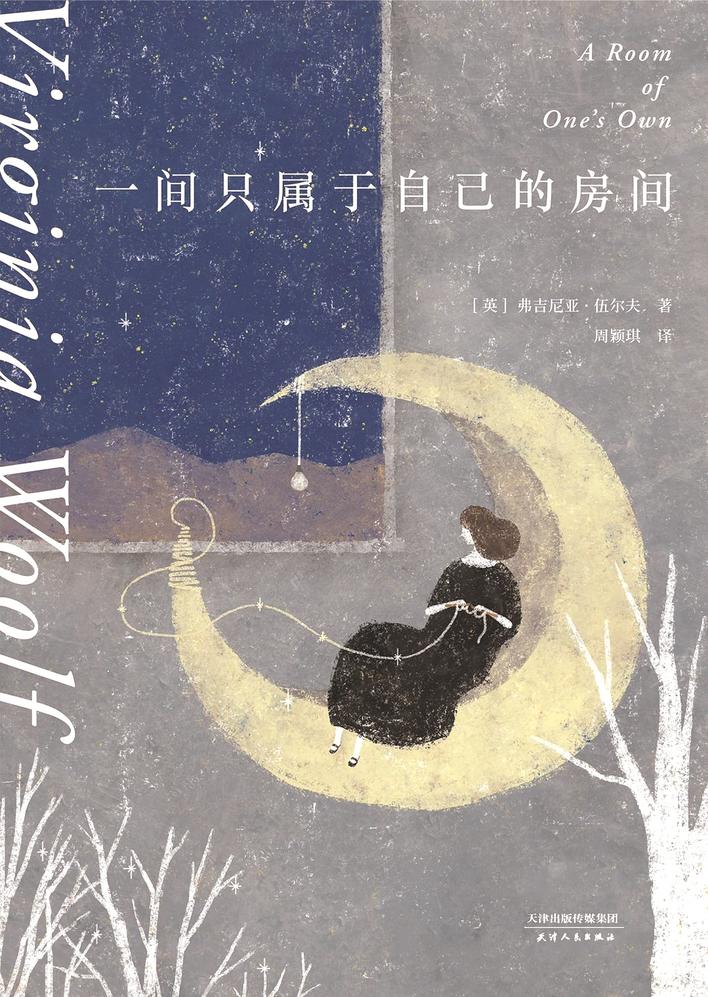□梅莉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集——《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29年,是由她的演讲稿编写而成。1928年,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作过两场演讲,主题是“女性和小说”。她却因生为女人,被拒绝单独进入图书馆,还被从草坪上赶了出来。毫无疑问,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地位是卑微而低下的,哪怕是才女伍尔夫。
读后依旧感慨万千,我要是在年纪轻轻时看过此书就好了,这样会早早领悟到金钱的重要性,而不是人到中年才幡然醒悟要努力赚钱、存钱。老公曾各种惋惜,你怎么不再是当初那个没有物欲、人淡如菊的温婉女人,而变成一个财迷了呢。我坚定地回答,不,我觉得年轻时漠视金钱的自己简直太傻了,现实让人清醒,如果没有钱,我连妈妈的保姆费都付不起。
文艺女性都有清高的一面,仿佛谈钱爱钱就降低了人格,有的作者甚至发表了文章没收到稿费都不好意去要。虽然我一直不赞成女性做全职太太,伸手向男性要钱,势必失去精神上的独立,但我也并没有努力赚钱的欲望,而是躺在工作的舒适圈,觉得养活自己就很好了,赚钱的事交给男人吧。一百年前伍尔夫的精神世界已遥遥领先于我,她一针见血地道出女性的种种困境均来源于贫穷。她真诚地劝告女同胞:“我希望,大家无论通过什么方法,都能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如今的都市女性实现这些并不难,而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可能这还是奢望。近年来因为自媒体短视频的盛行,很多女性也开始觉醒。比如六十岁的苏敏阿姨离家出走后,通过自驾游拍视频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价值,摆脱了糟糕的婚姻。首先是她经济上不再依赖于丈夫,才有享受看世界的自由。也有在大冰演播室里说“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到西双版纳,过个冬天”的麦子阿姨,她在爱心人士的接力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伍尔夫所处的男权时代,女性实在太贫穷了:“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与动荡……”还是女人心疼女人呐。女人想写小说,写诗,必然要遭到嘲笑与打压,她们的正业是生孩子与做女红。那时的女性进行文艺创作,只能遮遮掩掩,生怕被人发觉,因为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所以伍尔夫明确地表示,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她必须得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有钱不难,钱多钱少而已,但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谈何容易,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看过某位知名女作家的散文集,她在书中坦言迄今为止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而在伦敦某出版社工作了一辈子的著名编辑戴安娜·阿西尔,在其作品《暮色将尽》里也说自己买不起伦敦的房子,一直租房住。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们写散文、写小说,我想,主要是她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所以精神上也独立,虽然没有一间具体的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但在心理层面是有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非具体指向,而是指一直被社会忽视与压制的女性找到自己的位置,使写作不再是一件需要遮掩的事。她们在两性关系中也渐渐有了话语权,可以毫无阻碍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百年后,大部分女性地位的改变是令伍尔夫欣慰的吧。
伍尔夫说穷带给人的影响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是心理意义上的,穷会让人产生自卑、胆怯、忿恨,写作自然也会带着局限。她以自己为例,她的姑姑在孟买骑马摔死了以后,每年留给她五百英镑的财产,永久有效。当年的五百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四十万左右。在此之前,她是靠给报社做临时工谋生,写些无聊的报道。迫于生计,“做着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处处说好话,看人脸色,虽然没人强迫你这么做,但如果你不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想不到伍尔夫也有这样的经历,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害怕的失业吗。有了五百英镑年收入后,她也就有了安全感,心中的憎恨与痛苦消失了。“我不恨任何男人,因为他们不能伤害我;我不用取悦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给我什么。”她开始反省自己之前完全否定某个阶级或者性别都是一件荒唐的事。她连看待事物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从恐惧与酸楚转为怜悯与宽容,又过了一两年,连怜悯与宽容也已消失,“我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解脱,那是客观看待事物的自由”。忽然想起有个男同事,一直希望爆发战争,好像乱世中他就能分到某些富人的一杯羹似的,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中。伍尔夫阐明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带来悠闲和满足的心灵状态,也能带来创作上广阔的新天地,可以用超越性别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一百年后,虽然时代背景早已不同,但她认为物质基础决定心智自由、创作自由,鼓励女性自己去赚钱的观点,却一点也不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