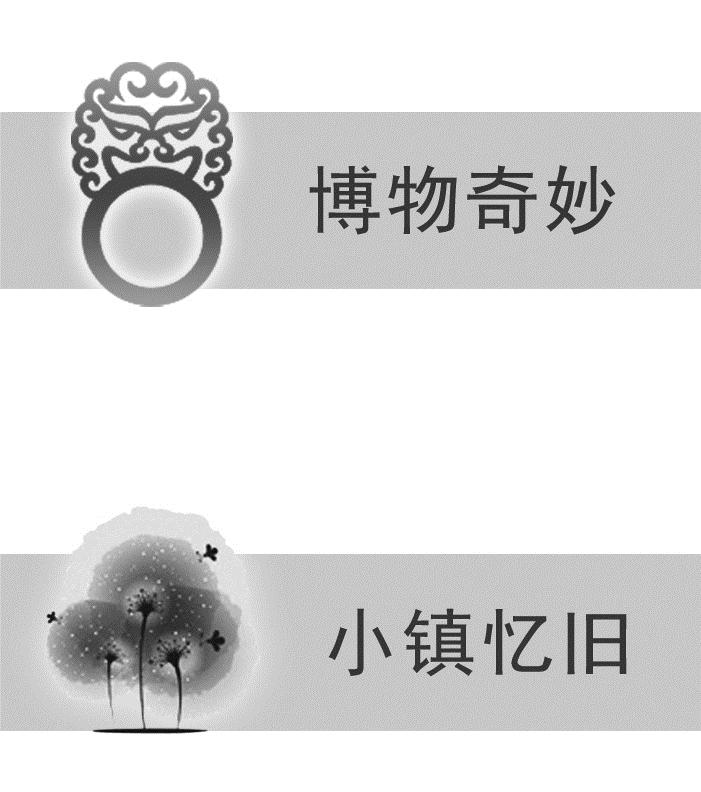□强雯
提到狂欢,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街头聚会,肉林酒池,毫无节制的画面。这要归功于现代媒介总是把狂欢标语和这一类的海报、视频拉郎配,并说自古希腊时代,众神狂欢莫不如是。百货商家、餐饮杂铺们也会趁机凑热闹,要释放自我,要买买买,于是乎管他符不符合国情,圣诞狂欢夜,情人节狂欢派对,盛夏嘉年华等一拥而上。乃至好几十年里,迷恋追求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小团体,也会时不时搞出些睡衣狂欢PARTY,诗歌狂欢夜,旗袍狂欢趴等,搔首弄姿口吐“文艺”。
于是醉也醉了,闹也闹了,虚无也虚无了,反省也反省了。但是总觉得现代的狂欢少了些什么,这只是给纵情声色扯一面遮羞布吗?
狂欢,从原始人时代便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国、印度、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和埃及,这些地方均有表现狂欢岩石艺术,人们手舞足蹈,庆祝着某种我们未知的事情。
狂欢,有时是自下而上的感染,比如岩画中的狂欢最早可能是为了御寒或御敌之故,渐渐成了一种规则、习俗。有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比如《史记·殷本纪》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长夜为饮”,这种狂欢将饮食男女糅杂在一起,虽然让商纣王落下了腐败的罪名,不过辩证地看,商纣王也是遵从了上古遗风,奔放的性自由是其表,摆脱人间劳苦是其核,君王和百姓一起,参与到与神同乐的事件中来。生死繁育,都是人间大事,也是国家大事。到汉代,逢着春节、元宵、七夕狂欢的文献著述更多,细读下来,无不是充满了“天下王土,非我莫属”的政治意义。
不过从考古遗址中走来的雕塑,更加佐证了我们对严肃狂欢的思考。宏大又精致的祭祀场景,活灵活现的人物肖像,从眼神到肢体语言,猪羊犬马,乐器酒瓶,狂欢元素应有尽有。他们手舞足蹈,他们叩天问地,严肃发自内心,快乐犹如天然。
最有声望的要数1955年-1960年出土于现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的青铜贮贝器。它是用来贮藏当时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海贝的罐子,类似于存钱罐。它夺人眼目的地方在于贮贝器盖上的诅盟场面。此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是西汉时期的作品。盖子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一次古滇人祭祀的狂欢场面。顶盖上铸有52个人物和一头猪、一只犬,中央立有一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一只虎。柱右和柱前是三个或被双臂反绑或戴锁枷的裸体人,当为用来祭祀的牺牲。坐在祭祀台的是古滇国能力超群的女巫,她手拿鸡卜卦,口中念念有词。在她不远处,一个个被捆绑的活人作为祭品即将被杀害。众多参与祭祀的人,神态各异,或垂手或抱肘,其中不仅有跪立受刑的奴隶,还有刽子手与押送奴隶的官吏。在祭祀建筑后面还放着两面巨大的铜鼓。
这祭祀的场面虽然血腥,但却是从上至下的狂欢,这广场犹如一个热闹的集市,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人神共乐。除了祭祀,这也是商品流通,商品交易的吉时,从雕塑上能看到,有的高鼻深目,有的蓄着长胡子,有的耳挂大环,有的头上顶着箩筐,还有牵着牛马驮着货物赶来的商贩,这一定是个好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参与这次祭祀,来互通有无,美酒美食,尽享其中。
古滇国是一个与西汉王朝同时存在的少数民族国家,在《华阳国志》中就有记载古滇国的风俗“其俗征巫鬼,好诅盟……官常以盟诅要之”。凡是有大事,古滇人都要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的典礼,是为诅盟。
这是最传统、最严肃的狂欢,敬天,敬地,敬众生。古滇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中享有声望,在祭祀的日子里,除了本地的滇国人,还有大夏人、三苗人来此地瞻仰威仪,寻找某种契机。
古代狂欢的雕塑类文物并不多,因此显得珍贵,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不过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狂欢文物。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文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契穆文化时期(公元900年-公元1470年)的双室黑陶瓶。整体高19.8厘米,长27厘米,宽14厘米。这个黑陶瓶分为两个部分,正面是一个水壶,背面是一个祭祀台。中间由一条弯曲的柳叶状的陶片连接。后面祭祀台底部有一个立方体基石,基石上站满了狂欢的各色人等,拿着打击乐器摇铃的,拍手鼓的,举手喝彩晃动身体的,地上还摆放着几个或立或倒的酒罐,有一个坐着的人正在捣弄酒瓶,这些人的眼睛硕大圆瞪,散发兴奋的光芒。载歌载舞的情形十分生动,愉悦。
而他们所面向的却是一个比他们都要高大的人物,此人物双手反相束缚,头上戴着新月形饰品,绑在那块柳叶形石条上,仿佛正在接受命运的安排或是即将到来的神圣。观者不禁会猜测,这是在祭祀狂欢吗?这个被缚的人是牺牲品吗?为何他的眼神也充满着兴奋的光芒?不过也有可能这位高大者是已故祖先的尸体。保存已故祖先的尸体并定期祭拜在契穆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为生者带来福祉。
此物现由位于秘鲁的拉鲁克博物馆收藏,因为2020年来到中国山西、天津、重庆等地巡展,才让国民大开眼界。
从这祭祀狂欢时刻的双室黑陶瓶中,回望契穆文化,也是十分璀璨。契穆人的首都昌昌古城位于秘鲁北部特鲁略市西北郊4公里的沙漠地区,占地36平方公里。“昌昌”在契穆语中代表太阳的意思。全盛时期昌昌拥有7-10万居民,是西班牙殖民者来之前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契穆国王以最高神明的代表自居,王室里的侍从分工精细,有伺候洗澡的 “侍浴”、吹海螺号角的 “司晨”、负责出行的 “司马”、在国王必经之路铺洒海贝粉的 “礼官” 等。分工精细,说明了契穆人在手工艺上的完备、优良。
同一行业的工匠毗邻而居。考古挖掘发现在同一个家庭中会同时进行金属加工和纺织,因此家庭中的男女都可能是工匠,但契穆社会禁止工匠改变其职业。工匠们所生产的产品除了供贵族阶层使用,还互相销售,又或者供居住在古城及周边地区的平民使用。
双室黑陶瓶,只是契穆文化时期无数精良陶瓶中的一个。
古往今来,从墓土中走出来的狂欢雕塑着实不多。这两款代表中西文明的祭祀狂欢雕塑,有某种相似。中国的是用来装货币的,秘鲁的是用来装水的。狂欢的人和神灵在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容器上,是副歌,是烘托,也是提炼和升华。因为这些容器都和人类的性命、生活质量有关,把祭祀的深远之意加固在这日常器物上,文物便拥有了格外的深意和能量。
狂欢,并不是单纯的消遣、娱乐,它严肃、敬重,是在此刻等着看见、听见神的话语;它是外在的恩赐,是人类值得争取的面包和自由。